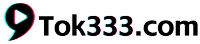责任编辑: 1718mu.com
前几年,在苏黎世与指挥家帕沃•雅尔维(Paavo Järvi)聊起他的家乡爱沙尼亚,他对我说:“你应该到帕尔努音乐节(Pärnu Festival)来看看。”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,今年夏天终于成行。
帕沃是当代国际乐界极有影响力的指挥家,除了任职瑞士和德国两个顶尖乐团的总监之位,还常年与世界各国的一流名团合作,比方说,并曾获美国格莱美大奖与德国古典音乐大奖。但他说,世界各地的住址,都比不上在帕尔努那种在家的感觉。到了指挥家度过童年的小镇去看过由他创办的音乐节,台上台下见帕沃的松弛状态,确实有褪下铅华,清风扑面之感。
探索波罗的海国度是我一个长年以来的愿望。为了逐寸感受地理位移,增加旅途的故事色彩,我特意安排了从伦敦出行、全程不飞的路线,经比利时搭火车到北德,搭船东渡波罗的海,在立陶宛上岸,再由拉脱维亚进入爱沙尼亚西南港口小镇帕尔努。
驱车经过爱沙尼亚-拉脱维亚边境时,车速丝毫不减,窗外飞快掠过已废弃十多年的边防站。同车里的前座是生于2003年的爱沙尼亚钢琴演奏界新秀Tähe-Lee Liiv,她头靠着座椅正在熟睡中。
这位20岁的新生代音乐家同时在伦敦和柏林学习,前一晚刚刚在威尼斯完成了一场演出。对比起来,1980年离开爱沙尼亚举家搬到美国的雅尔维家,代表的则是爱沙尼亚另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“爱沙尼亚位于前苏联的西部,在不能出国的时代,大家觉得到爱沙尼亚来就跟出国差不多了。”在苏黎世时,帕沃忽然提起自己7岁的时候见过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面:“他跟我父亲(指挥家尼姆•雅尔维)是朋友,那时他来我们在帕尔努的家。(小提琴家)大卫•奥伊斯特拉赫、(大提琴家)罗斯特洛波维奇他们都来过。我和父亲、肖斯塔科维奇三个人一起拍了张照片。”然后帕沃执意在手机里找了好一会儿,翻出来一张黑白照片。
在帕尔努期间,我特意找去大卫•奥伊斯特拉赫曾住过十多个夏天的故居,外墙绿漆已剥落,但院子里的树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苹果,这让我想到帕沃跟我说的:小镇生活还有许多过去时光的痕迹。再走一点,就是波罗的海的入海口,海草在风中狂野飞舞。
于是帕尔努,而不是首都塔林,就成了我进入爱沙尼亚的第一扇门。这个海滨小镇拥有一座专业音乐厅,但却还没有自己的火车站。据说一条贯通波罗的海国度的高铁正在兴建。帕尔努湾是整个国家惟一朝南的海滩,浪潮温和。在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下,扑面都是带双重字母和特殊语调标记的词语。除去这种具体印象之外,剩下的就是每场音乐会带来的抽象感受。来帕尔努之前,我只是从帕沃与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(Estonian Festival Orchestra)合作的CD中听过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世界首演录音。在现场亲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就拿当今爱沙尼亚作曲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托努(Tõnu Kõrvits)在音乐节上的新作《舞曲集》首演为例:我在看演出前刻意先不去看背景文字,手风琴响起时的小调旋律马上能令我联想起东北欧的民间故事来,印象派色彩的写意和弦,则带来山海间大自然的气魄。音色流转间,脑际还闪过这两天不断往返的帕尔努海滨林荫道、夜里11点还亮着的天,还有三两结伴的金发少女。每个晚上,音乐会结束后,乐手与观众们都不急着回家,而是涌到小镇中心的一家酒吧里喝一杯,长龙常常排到街上,队列中的陌生人就会自然开始聊天,等排到前面时大家都已经成为朋友。
 雅尔维父子仨:克里斯蒂安(左)、尼姆(中)和帕沃•雅尔维,摄影:kaupo kikkas
雅尔维父子仨:克里斯蒂安(左)、尼姆(中)和帕沃•雅尔维,摄影:kaupo kikkas 1980年,帕沃17岁时,与父母亲、弟弟和妹妹一块儿离开爱沙尼亚,移居美国。前苏联解体之后,雅尔维一家基本上又搬回了爱沙尼亚。14年前,帕沃在充满童年回忆的海边小镇创办了帕尔努音乐节。凭藉帕沃的影响力,他也陆续将世界各国的大腕艺术家们请了过来。
音乐节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及音乐节资金时说,爱沙尼亚转型才30年,并没有“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钱”,预算比起德奥等地的音乐节来差了一截,可是我所感受到的节目内容与水准,相比起来毫不逊色。
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作品自然是音乐节的焦点,但担纲主角的“爱沙尼亚节日乐团”,成员则是帕沃在各个乐团的爱将,包括苏黎世音乐厅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和慕尼黑爱乐的首席大提琴,以及柏林爱乐的低音大提琴。因为心意相通,指挥家与乐手们彼此合作融洽,尽管乐团一年一聚,音乐会却水准极高,尤其是观演体验,相比起在伦敦柏林等大都市的音乐会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帕沃对我说,他想营造出一种“专有”的体验:“但‘专有’这个词,经常被误解成是将其他人排斥在外。音乐节并不是一个会员俱乐部,但我们绝不会为了吸引更多听众而放低身段。莎士比亚、伦勃朗都不是精英主义者,但他们的作品都确实有一定的欣赏门槛。我们的乐团里坐着世界顶尖乐团的明星乐手,我们不放松任何排练,以保证节目水准是最高的。”
在帕尔努的四天里,我边感受边观察:这个节日吸引人们从爱沙尼亚各地及邻国芬兰、拉脱维亚甚至德国赶过来,大家沉浸与享受的,并不是因为这儿是香粉加华裳的风雅社交场合,而是因为音乐节与里加湾不太咸的海水、自行车和踏板车、腌黄瓜与白菜肉丸子无缝连接的生活气息。如帕沃所说,这里“没有金光闪闪,没有装模做样,现实的样子不多不少”,“真实”就最吸引人。
 大家沉浸与享受的,并不因为这儿是香粉加华裳的风雅社交场合,而是音乐节与里加湾不太咸的海水、自行车和踏板车、腌黄瓜与白菜肉丸子无缝连接的生活气息。摄影:张璐诗
大家沉浸与享受的,并不因为这儿是香粉加华裳的风雅社交场合,而是音乐节与里加湾不太咸的海水、自行车和踏板车、腌黄瓜与白菜肉丸子无缝连接的生活气息。摄影:张璐诗 离开前一天,我在乐团排练结束后到帕沃的休息室里跟他又聊了一次。帕沃向我递过来满满一盘的莓果,他助手提了一袋子樱桃和豌豆进来,帕沃开心地嚷着:“每年回来最惦记的就是樱桃”,然后向对着一颗大豆角不知从何入手的我,演示如何快速剥开豆荚的技巧。
帕沃已担任德国不来梅德意志室内乐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长达20年,他同时身兼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。从14年前起,每年7月他都有一段时间必在帕尔努度过,与父亲尼姆(Neeme Järvi)、弟弟克里斯蒂安(Kristjan Järvi)分担演出任务,白天除了与乐团排练,还给指挥大师班的学院授课。
克里斯蒂安•雅尔维跟哥哥帕沃性格迥异。在沉浸古典音乐世界30年、执棒过各国顶尖乐团之后,他决心投奔现代音乐,与麾下的“北方脉搏”(Nordic Pulse)乐团探索电子乐与即兴表演。克里斯蒂安以流行摇滚乐队的形式去操作一个管弦乐团的概念,在本届帕尔努音乐节上做了首演。一晚连演两场,所有门票售罄。相对于正襟危坐的古典乐现场,“北方脉搏”的镭射灯光和大音量称得上“叛逆”。但这也正是音乐节的独特之处:创办人帕沃与父亲、弟弟和妹妹同时出现在音乐节上,每一位家庭成员在乐界都独当一面,这样的“家庭聚会”尤显“仅此一家、别无分店”的珍贵。
同时在欧洲不同地区任职和生活,帕沃的体会是“瑞士较少出现缺失自我身份的困境。爱沙尼亚跟芬兰相似,经常有‘后院起火’的担忧,通过音乐去保护自我文化身份的需求就显得更迫切一些。”
爱沙尼亚处在重要的地理位置上,从前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曾将爱沙尼亚称为“欧洲的窗口”,坐拥芬兰湾,又直入波罗的海,无论军事还是贸易上都是战略要塞。爱沙尼亚在历史上屡遭侵犯:德国占领了八百年,上世纪又短暂占领了一段时间;丹麦、瑞典都入侵过;俄罗斯占领过两次。
眼下的战争万一向邻国延伸,爱沙尼亚将是第一个遭殃的国家”,帕沃说,惟一维护集体身份的方式就是通过音乐和艺术去实现。他提到,爱沙尼亚在世界上最有名气的个体是作曲家阿沃•帕特(Arvo Pärt)。爱沙尼亚作曲家尤里(Jüri Reinvere)则提到,创作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:“假如文化创作不能持续发展下去,作为一个国家的爱沙尼亚也会逐渐消失。”
音乐文化对于爱沙尼亚的身份独特性不言而喻。帕沃在帕尔努办音乐节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:他不希望下一代跟爱沙尼亚切断关系。在美国的家里,帕沃也只跟孩子们说爱沙尼亚文,不说英文。
我看的几场音乐会之中,曲目的安排意味深长。其中一首作品是爱沙尼亚“女性作曲家第一人”埃斯特(Ester Mägi)的《晚祷》,另一首作品则是拉脱维亚作曲家彼德里斯(Pēteris Vasks)写的《静默的果实》,这段作品以特蕾莎修女的一段和平祷告为蓝本创作而成。今日这首充满内省的作品在波罗的海响起,帕沃的用意不言而喻。
 帕沃(右)与爱沙尼亚节日乐团演出作曲家Pēteris Vasks(下)的作品《静默的果实》。摄影:kaupo kikkas
帕沃(右)与爱沙尼亚节日乐团演出作曲家Pēteris Vasks(下)的作品《静默的果实》。摄影:kaupo kikkas 以下是指挥家帕沃•雅尔维对话时的自述:
对于爱沙尼亚来说,文化最好的表现方式是音乐,那是一种对生存的确认。一个群体在一起,创造自己的语言、文化、艺术才能形成“国家”和“国籍”。尤其在民粹主义横行的今日,许多政权都在刻意边缘化文化艺术,如果我们不去持续创造出带有自我身份特征的艺术,具有原创性和个性的作品将会慢慢消失。
我们赖以生存的是语言和我们的歌曲。一个管弦乐团是拥有内在生命、传统和文化的机体。我祖母来自帕尔努,小时候每个夏天我们到这里过暑假。在这里长大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回忆。我记得在海滩、河边、森林周围荡悠,无忧无虑,夏天的日子像牧歌一样。想起人生中最好的时光,我总会想到这里。
我祖母曾经有一本小蓝本,里面全是古老的爱沙尼亚歌曲,她熟悉所有的旋律,我们跟着她,也学会了大部分的歌谣。有一首歌唱得是一位姑娘望着远航的帆船,她的水手哥哥在船上,歌中充满了伤感与渴望。很多的歌谣的主题都是“亲人被带走,从此再也见不到”。上千名爱沙尼亚人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,今天的西伯利亚村庄里还满是爱沙尼亚人。
当然你需要接受,新音乐并非都能立即引起大家共鸣,不像朗朗上口的流行文化,走到哪里都一个样。1990年代,爱沙尼亚实现第二次独立后,很多人都在说要找到“爱沙尼亚自己的诺基亚”(因为手机品牌“诺基亚”,芬兰创造了商业奇迹)。但我一直对此持有保留意见:诺基亚是可以被其他国家收购的,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芬兰,但谁都无法将阿沃•帕特(Arvo Pärt,爱沙尼亚作曲家)买下来,他将永远属于爱沙尼亚。重要的是象征,我们的国家这么小,但提起阿沃•帕特,大家都听说过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。音乐文化是无法被标价的。
 帕尔努的街景,摄影:张璐诗
帕尔努的街景,摄影:张璐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帕尔努就是个小城镇,但美极了,许多前苏联人也喜欢过来度假。有一些昔日世界的气质还在,但随着商业大楼不断盖起来,本地仅有的个性就快要消失了。时间的痕迹,可惜我们都逃不过这种所谓的进步。就像我们在世界上每个城市都能听得到的电子音乐节奏,在哪里都一样,这样的流行文化形式,似乎就是特意设计成为经不起时间推敲的样子,人们只顾着此时此刻能卖点钱。这个时代,我们那么容易就心甘情愿背叛个性、出卖个人隐私,以换取某些生活便利。
但另一些音乐,赚钱不是主要目的,而是为这个时代留下具有自我个性的原创艺术。音乐就是需要抽象,不需要鲜明的卖点,明确告诉听众:这里用上了民间故事,那里用上了俄罗斯小调。我们只需要作曲家的独特视角、以及他们作为爱沙尼亚人的表现手法。这很难去形容,但你一听就能听出来。
文章编辑: 1718mu.com